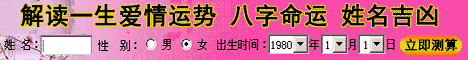|
看镜子,能看到自己,其实就是隔层水银,就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了。如今的社会比较可怕,总是遇到那种遮光镜,你看不到他,他看得到你想想就感觉很恐怖。本期的灵异故事,带你看看地摊上的镜子。
辉是我在日本认识的,当时我们的访问团缺少一个翻译,日本相关的协会正好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帮我们,我们团长一着急竟然在一个酒会上自行找起翻译来,辉是在日本留学的大学生,长得十分瘦弱,也需要打份工挣点零花,看我们团长邀请也就答应了。 辉在日本已经结婚,丈夫也是中国人,和她一样在留学。她忙不过来的时候也带上丈夫一起,帮我们当翻译。晚了,她也不回家,和我住一间房,她丈夫则和团里的男士挤着住。 那天晚上,可能是PARTY上酒精的作用,辉突然哭着和我说她不幸福,想回国,我想身在异乡,贫贱夫妻多有摩擦也是正常的,况且我也喝得有点高了,迷糊着听她说了很多,渐渐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去当地一座山上参观庙宇,山路上有不少小店铺,我和辉就进去逛,转着转着,辉就不见了。我想就在附近也就没有去找,我看见一个摊上有许多制作精美的小镜子,就看起来,突然背后有人对我说,你看看这个。我一回头,原来是辉的丈夫,就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是一小方扁的黑色东西,上面有绘的日本仕女图,背景上几抹樱花,觉得挺精致,就接过来打开一看,里面镶嵌着一枚方形小镜,就说:是不错,我买一个。 我们在日本的行程到期后,就准备回国。走的那天,辉来送我们,尤其和我道别时,我们两个都哭得不行,毕竟女人多愁善感,等我上了车,没看见辉的丈夫来送行,想想也没什么,可能因为忙吧。在日本这段日子行色匆匆,太多活动,我觉得自己一直昏沉沉的,说不出的疲劳,这下总算可以回家了,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回国又开始忙工作,日本之行很快就成了记忆,转眼过去一年多,有一天辉给我来了电话,我很惊喜,这还是我们分开后第一次联系,她在电话里说要回国一趟,如果方便要来看我。我说当然可以,并问候他丈夫好,问他是否跟他一起来。辉在电话那头很久没说话,我喂了几声,她说:我哪来的丈夫?我楞了:怎么?不是在日本你们一起给我们做翻译吗?那天,我记得一天晚上你还和我说你和他有点矛盾,他不是那天也住了酒店的吗?辉说:你看见他了吗?我说:怎么没看见,我们不都看见了吗?我突然就糊涂了,觉得所有的记忆一下子不可靠了。辉说:可能你弄混了吧,你们那段时间日程安排太紧,你又那么疲劳……我一时有错乱的感觉,就说:那你来了我们见面再聊。 挂了电话,我一刻没有耽搁,翻箱倒柜找那面镜子,这总不是幻觉的吧,我记得收拾在一个木盒子里,里面全是我买的一些小东小西,看厌了就都扔在这里,这镜子没实用性,不过是个旅游的纪念,记得当时就收在那里的。掏了半天终于在盒子底找出那面镜子,镜子是方形黑色的,开合式的,没错,就是这个,是辉的丈夫建议我买的。我有点哆嗦,想了想还是打开了…… 掏了半天终于在盒子底找出那面镜子,镜子是方形黑色的,开合式的,没错,就是这个,是辉的丈夫建议我买的。我有点哆嗦,想了想还是打开了…… 一看我惊得将镜子扔在里地板上,里面根本没有镜子,而是刻满了樱花,那种被涂得血红的樱花,整个里面都刻得满满的。当时我明明记得打开后里面就一面有镜子,另一面不过是黑色的。这是怎么回事。我的记忆出了问题了还是这是个什么鬼东西。不等细想,我弯腰拾起那个怪物,用尽了气力,从窗口直接扔了出去,我吓得额头都是汗,心跳得厉害,两腿直发软。 一个月后。 辉回国了,她回家一趟,又专程坐飞机往我居住的城市来,我知道她一定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而我更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约她来家里,见了面,我发现她气色比一年前好了很多,只是人神色有些抑郁的样子。我们一见面也不问候别的情况,直接就说起了镜子的事情。我先就前前后后说个不清,并指天发誓确实听见她和我述说和丈夫不和想回国的事情,也确实见过她丈夫,并且镜子就是她丈夫建议我买的。辉说让她看看镜子,我后悔不来,告诉她我当时看到镜子的变化吓坏了给扔掉了。于是又赶紧形容镜子的样子,以及回家后发现镜子的变化。 辉沉默了良久,告诉我:我没有丈夫,但我出国前有个男友,确实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我想出国,而他不愿意,我们有了分歧,于是就分开了。说等几年再说。我在日本也确实非常想他,后来听说他在国内结婚了,也就努力将他忘记。我说:那,那是怎么回事?对了,你这个男友什么样子?我看到的是谁,还有,怎么就我看到?我有点抓狂,慌慌张张地给辉倒了杯水,让她靠窗坐了,自己突然想起同团的好友丁强。我怎么从来没问过同团的人,毕竟团里的人不在一个单位,回国后很少联系,都各忙各的,现在打电话问不知道会不会吓到别人,琢磨好说词就拨了丁强的电话:喂?丁强吗?我是晓兰。怎么是你啊,大忙人,总也不联系,怎么突然来电话了?最近好吗?还好,我有件事情想问你,我们去年去日本的时候,有没有在当地找了个男的翻译,男的!翻译?男的?没有啊,你不记得我们和小日本拿英语对话的吗?当时翻译难找啊。这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说没有男的翻译对吧?你怎么了?没有啊。我再确认一下,没有男的翻译,只有一个女的翻译,叫辉,是当地留学生,是这样吧?没有,没有翻译,没有任何翻译,当时当地协会说找不到人,我们都用蹩脚英语对付着呢。你怎么了晓兰,出什么事情了吗? 我已经听不清楚丁强还在说什么,电话沉的要把我的手都扯折了。我艰难的转过头,看见辉正对着窗外看。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便语无伦次的开口道:关于那面镜子…… 辉回过头来看着我,展开手掌问:是这块镜子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