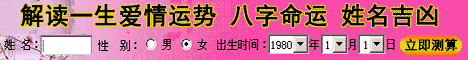对蛊毒最权威的认识(16)结语尽管今天汉人社会常常想象苗人放蛊,但是,汉人关于蛊的观念却有更为悠久的历史。汉人社会内部的巫术想象和指控曾长期存在。清朝末年,正定府(在今天的河北境内)乡绅李凤阁著有《驱蛊燃犀录》。直到今天,在福建一些地区关于放蛊的想象和指控依然存在。
蛊往往与疾病原因联系在一起。作为对疾病原因的推测,蛊的观念反映了人们的认识方式。从一种的致病之虫,到一类泛义的致病邪毒,再到没有明确界定的病名,以后出现病名与证候名相分离的用法,[1]“蛊”含义的转变一直体现了一种想象、假想的基本特点。中医对蛊疾的诊断长期以来就没有能够摆脱想象因素的约束。中医的疾病诊断使得巫术指控被蒙上疾病事实的外衣。
巫和蛊原本具有各自的意义。巫蛊的连用被用来指黑巫术。后来更多的是指一种与使用蛊虫有关的,或者说巫蛊是对一种用蛊的巫术的想象。
由于受到和的影响,汉人社会的鬼神观念演变。对疾病原因的想象和对用蛊黑巫术的想象的被结合在一起。志怪小说在这一结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医对“蛊疾”的治疗正是从对疾病原因想象和对黑巫术的想象这两个基础出发。这样一种关于邪恶的个人及其法术的观念也衍生出来。无论是在疾病理解上还是在巫术理解上人们都是对此感到恐惧。
疾病的压迫和想象中的邪恶者被联系在一起。这些邪恶者成了社会共同的敌人。无论是政府官员、巫师、医生、和尚、道士,还是志怪小说的编撰者、史书地方志的执笔人都将以自己的方式或控诉巫蛊者的邪恶和罪行,或抚慰诊治的人们病痛和猜忌,或传播预防的方式、应对的办法。他们如同畏惧鬼神一般畏惧邪恶的巫蛊。人们想象中有“蛊”的人被妖魔化。
明清以来汉人与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接触频繁。大量汉人移民从江南到达他们原来认为的蛮荒之地,面对不熟悉的自然环境和周围充满敌意的少数民族。他们遭受新的疾病和困难。中医对于这些疾病的解释和周围不友好的族群唤起了他们的历史上曾有的巫蛊信仰。他们用巫蛊观念来解释疾病,也用以实施针对少数民族的控诉和掠夺。李卉指出了这种关于少数民族的谣言的形成的一些原因。但是在细节分析上由于只能获得汉文文献资料,缺乏实地调查,不免有一些瑕疵。例如在论述瑶人蛊卦时作者不慎将瑶人巫术与混淆。[2]这种不同正如《周易》中的“蛊卦”与我们定义的巫蛊风马牛不相及一样。
这种对苗人的巫术想象不仅发生在作为移民者的汉人那里,也发生在诸多的“土著”中间。汉化程度更高的壮人、布依人、侗人等对于居住于高山的苗人也进行着有关苗人邪恶的想象。无论是汉人的想象,还是壮人、布依人、侗人的想象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加强族界,保持族群距离的实际作用。壮人、布依人、侗人在想象苗人巫术危险的时候,自身在汉人的想象中也是危险的。
王明珂先生在《羌在汉藏之间》描述到羌人中“一截骂一截”的现象。在巫蛊指控的族群链中,汉人想象和指控少数民族,特别是苗人施行巫蛊;而壮人、侗人尽管自身也被汉人想象放蛊,但是他们却也想象苗人放蛊。奇怪的是这种想象关系在族群间是单向的,汉人不会被想象成放蛊者。
明清以来,汉人大量地进入苗人居住的地区。在苗汉文化的交流中,汉人的巫蛊观念可能通过巫师和医术以及文学作品进入苗人社会,并被苗人内化。
巫蛊的观念由汉人巫师、医生、文人、以及受到此观念影响的苗人巫师(或者其他巫师)引入苗人社会,并与苗人社会原有观念结合。于是,形成了苗人社会的巫蛊观念。
从苗人社会的巫蛊传说的故事来看,它很可能是从汉人巫蛊观念转变而来。
那些房族小,社会关系差,声誉不好,迁居而来的人在苗人社会容易成为巫蛊指控的牺牲品。他们一般缺乏反击谣言的能力和条件。其中一些人则沦为备受排斥、指控的对象,并代代相传。苗人社会的巫蛊信仰形成了相关的婚姻禁忌。
苗人社会浓厚的神信仰,对祖先的崇敬以及淳朴善良,嫉恨邪恶的性格使得巫蛊信仰长期地存在,不能得到清除。
关于“蛊妇”的传说常常被置于两个极端之上,一个是美丽;一个是丑陋。都是区别于常人的特征。通过强调这种特征,也能强调她们的他者身份。对于美丽的“蛊女”,往往有性别意识的影响。对于一些麻风女也有同样的传说。此外,“蛊女”的容貌可能还有一定比例是受到近亲结婚的影响。被谣言中伤的人家常常被说成男俊女美。由于这些家庭的规模比平常家庭要很多,因此,笔者斗胆推测,他们对残疾子女有杀溺行为。有限的资源被用于抚养、优秀者。这些被主要通婚圈排斥的男女都有相当容貌,在近亲结婚以后,容貌的特点被加强。所以,“蛊女”的美丽除了极大的想象成分以外,可能还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对蛊毒最权威的认识(16)结语》由资料整理与编写,转摘请注明出处。
|